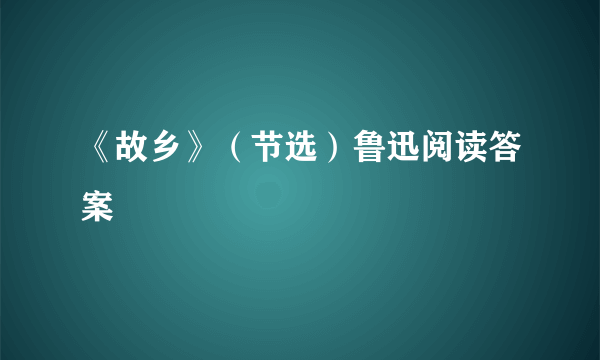鲁迅说:“杨朱无书。”杨朱是什么人?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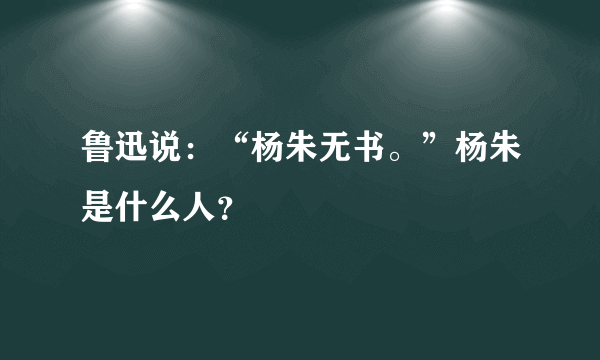
先说杨朱是何许人?有的说杨朱是战国初魏国人,有的说杨朱是老子的弟子。说杨朱是老子弟子的理由是:在《庄子》的<应帝王>与<寓言>篇中,有阳子居问道于老子的故事。有的学者认为:古代“阳”与“杨”通假,“阳子居”是“杨朱”的转音,所以就认为阳子居就是杨朱。 又因为《庄子》<山木>篇中有一个人物叫“阳子”,而杨朱又称“杨子”,所以又认为阳子就是杨朱。因此,通过学者的考证,杨朱就变得既多名又多事了。 老子是春秋人,杨朱既然拜了老子为师,这样一来,杨朱也就成了春秋人。杨朱是生在战国?还是长在春秋?也就变得多疑了。而《庄子》书中,常“杨、墨”并称,如<胠箧>篇云:“削曾、史之行,钳杨、墨之口。”庄子并不称“杨”为“阳”,故认定《庄子》书的“阳子”即是“杨子”,“阳子居”就是“杨朱”,证据尝不充分。 再说杨朱宣传何学?有的书上说:杨朱主张“贵生”、“重己”,“全真葆性,不以物累形。”杨朱确实“重己”,但并不“贵生”,更不“全真葆性”。其理由何在?且听下回分解。 有人把杨朱的学说列为道家,可能是因为《列子》中有一卷<杨朱>的缘故。因为《列子》属于道书,而<杨朱>又在道书之中,所以就误以为杨朱是道家了。其实,杨朱的学说不但受到庄子的指责,而且与<老子>也大相径庭。老子主张以“道德”为依归,而杨朱的学说并非如此。 杨朱的学说早已星散,好在《列子》收录<杨朱>一卷,虽不能窥其全豹,但也可以一叶而知秋,故权以<杨朱>为据而论之。杨朱学说中最有名的是“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”。其具体原文如下: “杨朱曰: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,舍国而隐耕。不禹不以一身而自利,一体偏枯。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,不与也。悉天下奉一身,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,人人不利天下,天下治矣。” 这一段分析起来很意思,杨朱的辩才也有此可见一斑。先看第一句,杨朱说: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”,为何“不以一毫利物”呢?因为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。既“舍国而隐耕”,又不参与世事,也不与人交往,自耕自作,自食其力,自然也就无从利人了。 伯成子高的事迹与泰伯很相似,泰伯也是“舍国而隐耕”,在《论语-泰伯》中,孔子说:“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!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。”“民无得而称”有二种解释,一种解释为:百姓对于泰伯的道德,无法用恰当言词来称赞。另一种解释为:百姓虽然没有从泰伯身上得到利益,但仍然十分称赞泰伯的道德。这二种解释虽然略有不同,但称赞泰伯“弃天下如敝屣”这一点,还是相同的。那么,杨朱从这件事中推断出了什么结论呢? 杨朱说:“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,不与也。”大家注意杨朱在此用了“障眼法”,把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”,偷换成了“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,不与也。”很显然这二句话的意思大差其远。如果以财富地位比喻“毫毛”的话,那么,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,能说是“一毛不拔”嘛?其实正好相反。古人道德高尚的事,到了杨朱口中,居然全然翻转,真可谓口舌如刀,言辩而伪。难怪庄子要钳杨朱之口了。 且说杨朱以古人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,推论出“古之人损一毫而利天,不与也。”显然不妥。但以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,推论出“悉天下奉一身,不取也。”到也合乎道家“弃天下如敝屣”的风格。那么,杨朱真提倡“舍国而隐耕”,清廉而自守嘛?却又不然。 何以见得?杨朱说:“原宪窭于鲁,子贡殖于卫。原宪之窭损生,子贡之殖累生。然则窭亦不可,殖亦不可。” “窭”音“据”,指贫穷。“殖”是货殖,指经商。杨朱说:原宪在鲁国受穷,子贡在卫国经商。原宪贫穷有损于身体,子贡经商有累于身体。所以贫穷也不行,经商也不行。 原宪与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,子贡经商而富裕,原宪清高而贫穷。原宪隐耕而贫穷,贫穷确实不利于养身,但富贵不可以妄求,不安贫又当奈何?子贡经商以脱贫,经商确实有累于身体,但衣食不自天降,不经商衣食何来?且原宪迹近于伯成子高,伯成子高“舍国而隐耕”,原宪也“隐耕”。为何说原宪也隐耕?因为原宪不仕不殖,清廉自守,衣食从何而来?故推断其由耕作而来。原宪贫穷有损于身,隐耕有累于身,伯成子高也一样,隐耕有累于身,清贫有损于身。另外,庄子的处境也与原宪相近似,安贫而乐道。庄子不以为忧,而杨朱却以为非。由此可见,杨朱之学与道家相差远矣! 杨朱说:“其可焉在?曰:可在乐生,可在逸生。故善乐生者不窭,善逸生者不殖。”这话是说:“要怎样才行呢?要生活快乐才行,要身体安逸才好。所以,善于享乐者不贫穷,善于安逸者不经商。说得到不错!但问题是:善于享乐者不贫穷,财从何来?善于安逸者不经商,食从何来?莫非会天上掉下来不成? 说到杨朱提倡不事劳作,安逸享受,与老子提倡的“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”相违背。因此,要把杨朱归入道家,恐怕很困难。要把杨朱说成是老子的弟子,恐怕也很困难。 或许有人会说:杨朱所说的“乐”,是指“安贫乐道”的“乐”,而不是“贪图享乐”的“乐”。杨朱所说的“逸”,是指“身劳心逸”的“逸”,而不是“贪图安逸”的“逸”。如此理解,粗看也通,但细究并非如此。因为杨朱说:“窭亦不可,殖亦不可。”贫也不可,劳也不可,分明是指身贫与身劳皆不可。杨朱又说:“善乐生者不窭,善逸身者不殖。”“不窭”就是不贫穷。“不殖”是指不劳作。“不窭”、“不殖”分明又指不可身贫与身劳。所以可知杨朱提倡的安逸享受,与道家提倡的精神修养是大有区别的。 因此,杨学的漏洞也就显现出来,杨朱一面说:“悉天下奉一身,不取也。”那应该自耕自作,自食其力才对。一面又说:“子贡之殖累生”,“殖亦不可。”又应该不事耕作,不食其力才对。既曰不取于人,又要不事劳作,不知享受安逸的衣食酒肉从何而来? 所以杨学因此产生的矛盾,也就因此产生了流弊。纵心所欲而不事劳作,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呢?孟子亲历其危害,那就是:“仁义充塞”,“人将相食”。也就是造成了社会不顾道德,巧取豪夺的风气,其后果是多么严重啊! 由上可知,杨朱的学说自成水火,难以自圆其说。因此可见杨朱所谓:“人人不损一毫,人人不利天下,天下治矣。”不过是徒逞口辩而已,不但难以实行,而且连杨朱自己也难以做到。不象墨子的理论,墨子是亲自实践而且做到的。杨朱则不然,说“人人不损一毫”,不过是不以一毫利人的借口,并非自己也不去损人一毫。 要想不损人一毫,就得要清廉自守,而要想衣食无忧,就得要不辞辛劳。既想着安逸,又想着享乐,结局不外乎二:一、饥寒而死。二、巧取豪夺。能够忍饥挨饿,必为清廉之士,而为清廉之士,必不享乐安逸。然而清廉贫寒,又非杨朱所乐闻。杨朱说:“伯夷非亡(音无)欲,矜清之邮,以放饿死。”“清贞之误善若此”。再加上杨朱对原宪的评价,“原宪之窭损生”,可见其不赞清贫。那既要安逸,又不穷困,还要享乐,衣食何来?想来路也只有一条了。